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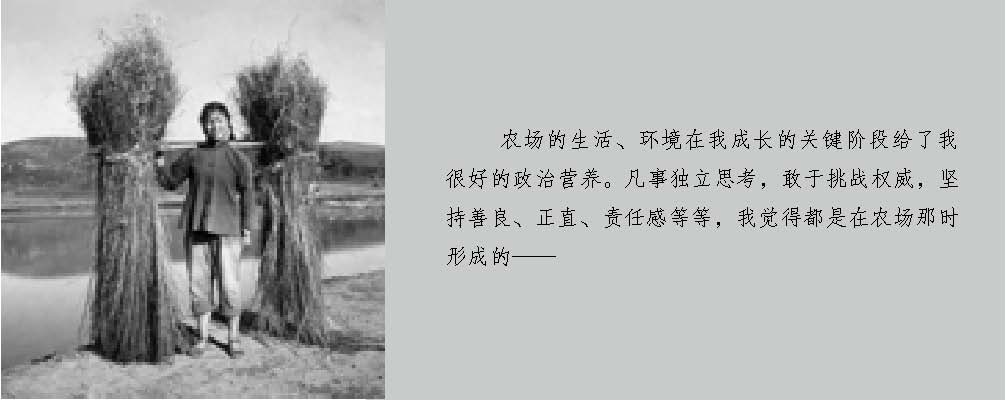 回忆青春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一队/ 杨百瑾 2009 年是我们上山下乡40 周年纪念。5 月15 日,我们当年陇川农场的知青聚 陇川农场的父老乡亲——我们基本上都是对家庭尽责,对社会有用的人。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我们一直都在向你们看齐,努力做一个大写的人。40 年后的今天,我们300 多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再一次集合起来,向你们致敬!再致敬!请接受全体北京知青的敬意吧,陇川农场的父老乡亲! (纪录片《回陇川》解说词 改编:沈芬) 2010年5 月15日在一起,纪念这个日子。 40 年前的这一天,我们一起乘坐专列,离开北京,5 天火车,6 天汽车,再加上中途因有人打架闹事,被办了两天学习班休整,整整13 天的长途跋涉,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陇川农场。40 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已两鬓斑白,大部分人已经退休。大家相聚,兴奋异常,陆续离开那里以后,有的“昔日战友”已经30多年没见了。 我离开农场比较晚,1978 年恢复高考上大学才离开。之后,我回去过两次。2003-2007 年,我又在云南工作了4 年,特别是2007 年8月调回北京时,我又专程告别性地回去了一次。 因此,这次会上,我向大家介绍农场现在的情况,放了一些我照的照片——当年大家熟悉的路、熟悉的房子,熟悉的大田、熟悉的人。 我也找出一些当年的老照片,或扫描或翻拍,通过电脑放到大屏幕上。青春的记忆一下被唤醒,很多人都被触动了。当年,我们队一个男生带了一台135的照相机,所以我们的照片大部分是生活照、劳动照,特别珍贵。 这次聚会一共来了70多人。一些人相约,万里迢迢,重回农场。从聚会后的第二天开始,回访农场的人便陆续出发。 重返陇川农场(一) 2009年是我第五次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农场探望了。我1978年春天离开那里,之后于1990 年、1996年、2004年、2007年先后回去过。想想,我确实把那遥远的边疆当成了我的家乡,无尽地眷恋和牵挂,隔几年就回去看看。前两次是我一个人回去的,2004 年春节那次是和老公一起(我们是一个队的知青),大年初一就是在陇川过的;2007 年那次有单位的一个同事陪我。这次很大的不同,庞大的回访团连家属一共有56 人,农场官方隆重地接待安排。 第一个感慨是云南的交通。当年,相比北京学生上山下乡的其他地方如山西、陕西、内蒙古、黑龙江等,云南农场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且怒江、澜沧江、瑞丽江上三座边防部队把守的威风凛凛的江桥,没有边防通行证是谁也别想过去的,绝了那些想私自跑回家的念想。 我们第一次从北京到陇川一共用了13 天,1972 年我回北京探亲那次15 天才到家(中途换车时买不到车票)。据说原来规定,因山路险要,客运班车一天只能开5 个小时左右就要住店休息,所以昆明到陇川的班车要6 天才能到达。 1990年那次,路还是那条上世纪40年代修的老滇缅公路,但已经有了夜班车。我从邻县瑞丽傍晚上车,两个司机轮流开,第二天晚上就到了昆明。那时还没有豪华大巴,休息的司机有一个改装的床可以睡觉。但我们在窄小的座位上一直坐了27个小时。 2004年那次,大保(大理——保山)高速公路已经通车,我和老公开着单位的车,从昆明一天(10个多小时)就到了芒市(陇川县所在的德宏州州府)。 现在,昆楚、楚大、大保,一路差不多都是高速公路了,回访团的同学们,坐一辆大巴,一天就轻松从昆明到了瑞丽(离陇川还有半小时车程)。而我因赶时间,早上从北京飞昆明,接着从昆明飞芒市,汽车再两个多小时,当天就从北京到了陇川。原来万里之遥的西南边疆,十多天饱受旅途劳顿的行程,现在变得如此简单轻松。 农场内的道路也早已全是柏油路面,四通八达,不再是当年的“扬灰路”和“水泥路”了。那时,雨季要出门,包括走着去总场和县城那样的大路也是不能穿鞋的——鞋会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再一个感慨是农场的热情。这次全部是农场官方接待,精心安排了3天的活动。举行了座谈会、联谊会,参观糖厂、学校、安居工程,到各分场、生产队走访,为早年在农场去世的知识青年扫墓等等。50 多人3 天的吃住全包,而且特意安排景颇族特色和傣族风情的农家乐,边吃边欣赏歌舞表演,让我们重新领略边疆的民族特色。农场还送我们每人一大包当地的蘑菇和茶叶,房间里摆放了很多芒果、山竹等热带水果。当然让我们感到更温暖的是热情的老领导、老职工的热言热语。 农场对知青的关爱是无条件的无功利的对子女式的关爱,让我感到自己为家乡、为农场想得太少,做得太少。 重返陇川农场(二) 在农场欢迎北京知青的联谊会上,我们集体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我心中的陇川——纪念北京知青赴云南陇川农场四十周年》,作者是我们之中一位在农场生活了10 年,后在农场中学当老师的知青刁松泉,还有些人对诗进行了修改。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表达了我们对陇川的基本感情。 当然,感受是复杂多样的,每个人不尽相同。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历史纠结在一起,更是有很多不容易说清的东西。 今年是我们上山下乡40 周年,同时也是知识青年大返城30 周年。1979 年,在全国各地知青特别是云南知青不断地上访、闹事,甚至绝食、卧轨……日益激烈的返城诉求下,中央终于下了决心,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开始了知青大返城。 对这历时10 年(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 年代初期,甚至更早)涉及上千万年青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作为当事人本身的知识青年,也有不同的心态和感受。我们这小小的陇川农场,300多个北京知青每个人情况就千差万别,有不到一年就“远走高飞”的,有在当地扎根结婚成家的,有幸运地被推荐上大学的,甚至还有因病和意外事故长眠在那块红土地上的。我没有从国家、社会、经济、一代人怎样怎样这些高度专门研究和思考过,也没有与同学深入讨论过——回京后这30 多年每次相聚,大家热热闹闹,并不谈论沉重的话题。仅从了解的身边的一点点情况,从自己9 年知青生活的切身感受,从40 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时的直觉,从重返农场座谈会上和下生产队时见到老职工时感人的场面,从我们齐声朗诵《我心中的陇川》时涌出的亲情和感动,我认为对那段历史,我们更多的感受是青春无悔——尽管生活艰苦、历经磨难、甚至也可以说岁月蹉跎,但我们确实没有更多可抱怨的。 在那时动荡的社会和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我们无所适从也别无选择。广袤的大西南边疆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垦荒队员、转业军人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建立起的农场,  作者在食堂工作时每天要从井里打200 多桶水 以它宽广的胸怀和发自内心的热情,接纳了我们。 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都一样。同样是挣那一份工资,比起还要养家糊口的老职工,知青的境况就要好多了。同样是食堂打一份没有油水的菜,老职工家还有五六个孩子要一起吃。但是老职工家难得杀了一只鸡或是辛苦一整个星期天淘干一池塘水捉几条小鱼,还有自己腌的各色咸菜,很多知识青年都去分享过。我们一去就住上了瓦房,虽然只是屋顶是瓦,墙是土坯的,但当时还有很多老职工住的是茅草房。 劳动虽然繁重,但没有强迫和虐待。更重要的是平等,有了发挥知识和特长的机会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知识青年老职工子女是同样的,好像还更受重视一些。陆陆续续,不少知识青年当上了生产队的文书、会计、卫生员、司务长等等,还有不少知识青年离开了生产队,担任机耕队的拖拉机手、医院的护士、学校的老师、宣传队的队员、场部的干事等等。后来,还在大田劳动的北京知识青年就比较少了。 这种平等和信任是很难得的。北京到边疆的知识青年,有“根正苗红”的,但大部分多多少少背着政治包袱——主要是出身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人受到牵连,父母一点事没有的在我周围是不多的。北京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的分配,第一批是去工厂,记得大约有近一半的同学令人十分羡慕地去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市制药厂等。这种天壤之别的分配,那时没有什么争议,你自己家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的,连想法都没有。别说去工厂了,我连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准部队)都没有得到批准。分配去了云南我还安慰自己——还有要去云南没有得到批准的,能去边疆,政治条件还不是最差的。 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直压着我们。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审往往过不了关。队里的老职工,对我们的家庭情况虽然知道一二但并没有任何歧视;农场自然就更清楚了,但在培养使用等方面也都是一视同仁。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大气候中,农场相对宽松的小环境;老职工的善良宽厚;基层干部的正直公平,多少次温暖了我们被伤害过的敏感的心。 1973 年大学恢复招生,群众一致推荐了我,但报上去后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这等于公开了我的问题,开始我灰溜溜的,甚至心里有点恐惧。但大家并没有议论或看重这等于是政治上宣判了死刑的“政审不合格”的结论,安慰我,鼓励我,使我并没有感到抬不起头来。1974 年招生又开始了,我犹犹豫豫不敢再报名,大家都鼓励我督促我,明明知道我“不合格”仍推荐我。当然又被刷了下来。 1975 年仍是如此。农场的干部和群众无力改变大的政治气候,我最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学走的,但那几次推荐,在那种情况下给予我的认可和肯定,至今令我难忘。 1975年支部发展我入党,在分场党委书记(当时兵团建制的营教导员)
作者保存的当年陇川农场工作证 杨某某的明确反对下,支部大会仍以18 票赞成,3 票反对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党委书记投了自己的一票反对票,这在今天也不可想象——党委书记反对,还会有18个人敢于违背书记的意志。当然我最后也没能在农场入上党,估计在党委会上也会与支部会的结果一样。那个杨某某一直没敢开党委会审批党员,直到后来全省冻结,直到我离开。 “文革”后期,陇川农场的“路线斗争”(当时就是这么叫的)与云南全省一样,是异常复杂激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农场的两个派头头分别被判刑10 年和15年(现在看有些过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一大批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并且敢说敢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基本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是在关键时候形成的。我到农场时才16 岁,虽然从北京来,也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确实什么也不懂,政治上又先天不足。但是农场的生活、环境在我成长的关键阶段给了我很好的政治营养。凡事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坚持善良、正直、责任感等等,我觉得都是在农场那时形成的。 当我1978年初进入大学以后,以一个与年龄和经历并不相称的极热情极认真的姿态开始学习生活和社会工作时,很多人说我不像是在农村呆了9 年的人,意思是我经过他们想象的磨难,应该油滑、消极、沉沦、看破红尘等等。 9年的知青生活,朴实的农场干部职工,教会我的恰恰不是这些。 所以,在从陇川走出来时,我没有失去追求,没有失去热情,没有失去要做一个好人的基本信念,我觉得这是我对那段历史最主要的无悔之处。
|
技术支持:信动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 京ICP备12025178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5847号 )
GMT+8, 2024-4-27 21:53 , Processed in 0.098005 second(s), 16 queries .